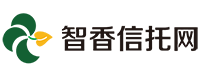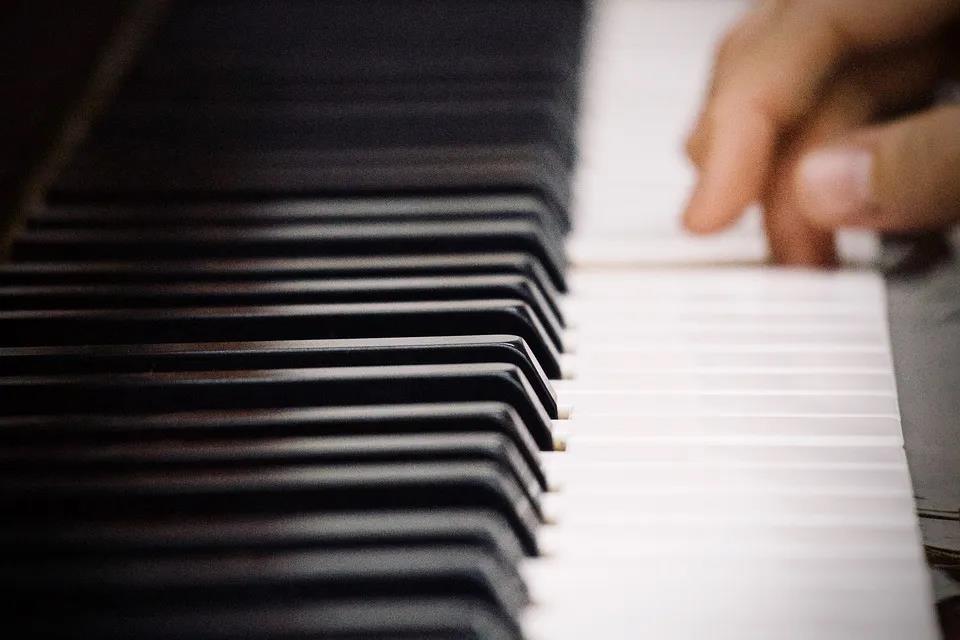

来源:一一道出
01
确定自己的生态位
我对团购网的混战印象很深刻。那年我刚大学毕业,也就是2009年。我在好多个团购网上都下过单,有的甚至下完单没再用过,连名字都忘记了。每次用哪个团购网,取决于临时看到的是哪个网的广告。
然后隔了两三年,作为消费者的感受是一夜之间,大部分团购网似乎都销声匿迹了。很突然的,我再去下单,选择就那么几家了。
后来看团购大战的数据,当时有1000多家团购网参与混战,而最后的收官之战呢,就只有10家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最初战场有多惨烈,很多公司在上演方生方死的戏码。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大部分公司都死在了战场上?
梁宁给出的分析角度很有启发性。混战中的大部分公司,其实都属于草莽企业。
任何一个行业在开局阶段,往往都有数不清的草莽企业。这些草莽企业进入行业的速度非常快,大部分当然死得也很快,很有点“春风吹又生”的意思。
草莽企业为什么速生速死?很多行业刚起步的时候,门槛低,大部分小公司都有力量杀进来。有些时候,可能行业的开创者就是一个草莽企业。写个开头很容易。
接下来,涌入更多的竞争者,这个时候想生存下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想在混战中脱颖而出,拼的是速度和狠劲儿,这是“闪电战”阶段。
美国顶级风投合伙人霍夫曼写了一本书《闪电式扩张》,就是讲草莽企业怎么通过闪电战突围而出。众所周知的亚马逊,在早期并不是走的精耕细作之路,而是一旦看到机会就迅速入场,一旦入场就做出大规模的投入。
霍夫曼说:“创办一家公司就像跳下悬崖,在下落过程中组装一架飞机”。这句话准确的形容了对草莽企业速度的要求,一定是快准狠。
有能力扛过混战,能好好活下来的,会成为下一个物种:腰部企业。这是大部分公司的生态位。它们构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腰部企业虽然很少会像草莽企业那样速生速死,但也并不会高枕无忧。
梁宁举了早期格瓦拉电影票的例子。2010年,格瓦拉拿到了上海电影票15%的市场。2011年,格瓦拉扩张到了北京等5个城市。当时整个在线选票程序还不成熟。只有20%的电影院加入了在线选票。至此,格瓦拉触到了天花板。
2014年,电影选票的内部壁垒打通了,一个接口就能连接起所有影院的在线系统。按道理来说,入行早,又已经到了腰部位置的格瓦拉,应该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人掀了天花板,不就该一飞冲天了吗?
遗憾的是,格瓦拉反倒迅速衰落了。因为可怕的巨头们入场了,阿里、腾讯。格瓦拉遗憾退场,但公司卖出了几十亿。这是腰部企业的厉害之处,不会像大部分草莽企业,说死就是真的彻底死了。
梁宁认为,对腰部企业来说,能让它们稳占生态位,甚至是突破生态位的方法,是和周边环境建立更加千丝万缕的关系。
举个例子,拿云南菜品牌云海肴来说,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了300多家分店。云海肴非常擅长做链接,和各地的大商场有着非常高效顺滑的对接流程。
这就是为什么云海肴能开在各大商场。而这个选择,也决定了它的规模。客流量非常稳定,而且几乎没有淡旺季。和它同期出道的茶马古道,坚守北京后海,10年后已经不闻其名。
想办法建立更多的连接,甚至是附着在一个生态位上,比如云海肴选择了附着在Shopping Mall上,这是适合腰部企业的药方。
如果格瓦拉能冲出腰部的生态位,就可以进入头部。头部企业干得是什么事儿?它们往往能终结一场混战。
还是拿当年的千团大战来说。最后胜出的美团、大众点评等,就直接结束了千团大战。团购网的风口彻底关闭了,自此,再也没有草莽企业会杀进来横冲直撞。
再拿我们熟悉的共享单车来说,最开始也是混战,最后同样是杀到最后的头部企业终结了战争。
头部企业代表了行业的高度。只有做到头部,企业品牌才会挤入消费者的心智。比如,现在咱们提到奶茶,想起的第一个品牌是喜茶,提到烤鸭,想到的是全聚德,提到火锅,想到的是海底捞。
但是,你别以为头部企业就是最牛的。生态位顶端的,其实是顶级玩家。什么是顶级玩家?那些能跨越周期的头部企业。
换句话说,那些能够突破增长瓶颈,进入第二增长曲线的头部企业。比如阿里,跨越了三个周期,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现在的智能商业。这就是顶级玩家。
对于很多顶级企业来说,他们面临的不再是来自行业内部的竞争。因为他们早已杀出重围,成为了消费者心智中的前三名。
未来真正能杀死它们的,是行业的周期迭代。
比如曾经的诺基亚,杀死它的是智能手机,而不是任何一家做普通手机的企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会有危机感。一旦周期跨越失败,顶级企业也会轰然倒塌。
跨越周期,是最难的事儿。你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它可能目前还没出现,或者即使它出现了,但和你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谁能想到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甚至把自己干趴下呢?
梁宁对企业生态位的分析,从草莽企业、腰部企业到头部企业、顶级玩家,其实对应到我们个体发展中也同样成立。
当我们出入社会,就是一家草莽企业,这个时候靠得就是学习、成长的速度。到了腰部阶段,就要在所在行业稳扎稳打,想办法建立更多的资源、人脉链接。
等到了头部阶段,也就是成为领导了,要想办法跨越自己的周期,比如,心理周期,情绪周期,行业周期。比如,如果行业都要沉没了,在头部还有意义吗?
好,跨越周期,就成为顶级玩家了。
作为顶级玩家,这一生,要始终保持对周期的敏感性,能够努力看到10年、20年后的大趋势。
这就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成长策略。对草莽阶段管用的策略,对腰部玩家可能就是致命的。
所以,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一定要先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02
发现和抓住机会
对企业而言,在发展中,会面临无数次的抉择。怎么样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机会,又如何抓住这些机会,从而让企业更上一层?
我们先来说如何发现机会。我们普通人对机会非常不敏感。有时候即使机会扑面而来,也未必能看得见,更别说主动出击去寻找机会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缺乏相关的能力。事实是,我们缺乏相关的科学方法。
梁宁在课程中介绍了一种发现机会的方法:穷举发散法。
她举得例子是自己工作坊的亲身经历。京东金融想做一个适合大学校园的产品,团队一共派出20人到了工作坊。梁宁把20人分成了四个小组。另外,每个小组还邀请了1名大学生参与。
接下来,进入穷举发散的阶段。所有人都要在便利贴上写下大学生在校园会做的所有事儿。不过在写之前,要把校园生活切割成一个一个颗粒度足够细的独立场景。注意,不能是上课、吃饭,参加考试、社团活动等这些概括化的场景。
场景的起止点是入学,场景的终结位置是毕业。中间根据学期阶段性再进行切割。颗粒度要要细致到,比如收到入学通知书,筹集学费的场景。
切割场景后,四个小组一共列出了460件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再把这460件事情,根据场景分成多个小主题,比如学习、社交、宿舍等等。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去寻找这些事情中存在的痛点、痒点或者爽点。能满足这三种的解决方案,就有可能是产品机会。
一套流程下来,整个团队一共找到了20个机会。最后,又邀请了100名大学生对机会进行“客观校验”,当场枪毙12个机会。
在剩下的8个机会里,又通过投票选出了需求最多的校园版58同城产品。这些真正的潜在客户,会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机会,哪些又是假机会。
这是寻找机会的一套科学流程,从穷举发散,到一步一步的排除,确保了能找到足够多的机会的同时,也尽可能确保发现的是真正有需求的机会。
好,发现机会后,就到了抓住机会的阶段了。到底应该怎么破局呢?从0到1,是最艰难的阶段。
这个信息发布的平台,应该发布哪些信息?最开始又要先发布什么信息来启动整个项目。团队筛选了100多件事情,本来以为已经找到破局点了。
结果后来发现,这些事情频次都非常低,比如找人修电脑,去火车站接人,这都是机会半年到一年才发生一次的事情。
低频会导致什么效果?大家很久才需要打开一次信息平台。这意味着,这个平台很难成为学生高频使用的工具。而且,极有可能被忘记。
再次筛选过滤后,发现最高频的是课程表,每天都要至少看两次,上午和下午的两张课表。到这个时候,才敢说找到了机会的破局点。
对于大部分产品来说,破局点一定要从高频切入。覆盖的人群也要足够广,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使用,产品规模很难做起来。
如果足够高频、覆盖人群足够广,恰好又是一个有强需求的新品类,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全民爆品。比如当年的智能手机,现在的喜茶等,都是开创了以新品类。
成为爆品后,再用口碑推动发展成为一个品牌。自此,企业有了护城河。而顶级的品牌,会成就一代商业传奇、
从发现和抓住机会,都有一套可操作性的流程方法,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我们肯定也注意到了,有些人发现的可不是这些不大不小的机会。
他们可是发现了一整个行业,然后劈开生死路,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行业,比如阿里巴巴的网络生意,腾讯的微信等等。这些机会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梁宁说,发现大机会,靠得是知识结构与精神结构。
什么意思?举个例子,我们来了解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诞生。1987年,张晓彬到美国访问了30多个城市。在访问中,张晓彬对美国的股市印象深刻,和朋友说,美国最好的东西是股市。
之后,张晓彬和朋友们开始行动,成立了中国证券交易所联合办公室。
为什么张晓彬能看到股市这个机会?相信那个年代到美国访问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只有张晓彬抓住了这个机会。这和他的知识结构有关。
机会需要识货的人识别出来。而识货的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眼力,是因为他具备了相关的知识结构,懂得这个机会是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
当年互联网的机会,有几个人笃信呢?1999年,马云从北京辞职到杭州创业。
当时合伙人什么状态?彭蕾说,大家眼神是迷茫的,空洞的。而当时的马云却放出豪言,说要做一家伟大的公司,站在桌子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
早期不论多艰难,马云都始终保持乐观。看到机会,懂得这是一个好机会的人,才会矢志不移的走下去。
这依赖的不只是知识结构,还和一个人的精神结构有关。是不是够坚定,意志力是不是很强,够不够乐观等等,都可能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对个人来说有什么启发呢?
我们要想发现和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去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是一个人的天眼,也是一个人的天花板。有了知识结构,精神结构也要跟得上,否则,照样会垮。
能把机会做成品牌,难度远远大于发现机会本身。
发现,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动作,而做成品牌,却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攻坚战以及守卫战。
只有知识结构和精神结构都过硬,才可能扶摇直上。
03
建设组织共同体
前面我们说了企业所处的生态位、如何发现和抓住机会,这些对一个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我们还得关注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一个组织有没有承接机会的能力。
如果没有承接机会的能力,即使发现了机会,最终机会可能还是会不翼而飞。
来看一个让人唏嘘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19世纪的淘金潮。
瑞士人苏特尔组织了一只探险队,到达了当时还非常荒凉破旧的旧金山。苏特尔很有胆识,从当地政府手里租了一片土地,租期是十年。在这片土地上,苏特尔带着自己的探险队开始种粮食,养牛羊。在这期间,财富自然是逐年增长。苏特尔还带着探险队修建了道路、桥梁。
1848年,探险队中的一个木匠,在挖泥沙的时候发现了金子。苏特尔告诉大家要保守秘密。有人听吗?没有。探险队的这波人,都扔下了手头的活儿去挖金子。很快,闻讯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淘金潮开始了。
土地上的粮食、奶牛,都被大家抢走。几乎是一夜之间,苏特尔十年的辛苦付之一炬。
1850年,苏特尔起诉要求收回自己的财产。五年后,案子虽然胜诉了,却没法执行。他既没有办法收回土地,也没办法收回自己修建的道路设施,当然也没办法获得淘金的分成。
梁宁说,这是她在讲组织时特别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很多人喜欢甩锅给机会,认为自己失败是机会没来。真正的事实是,很多时候,机会从天而降,大部分人也未必能接得住。
苏特尔并不缺乏机会。然而,当更大的机会砸过来后,苏特尔根本没办法接住这个机会。因为更大的机会,需要一个组织去承接,这样才能完成个体没办法去完成的事情。
你需要有强悍的组织能力,才能抓住机会。
要注意的是,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并不是一个概念。组织能力,更关注的是组织者如何把一个个个体,团结成一个大的整体。管理能力,更关注的是一个组织执行规则的能力。
一个讲关系,一个讲规则。组织能力强,未必管理同样出色。管理好的,也未必组织能力强。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组织有没有共同理想,是决定组织能力的第一个要素。
马云说:“三流的组织靠共同规则,二流的组织靠共同利益,一流的组织靠共同信仰。而最典型的好组织能做到至情至性”。
我们经常听阿里公司的人自称“阿里人”。在今年疫情期间,阿里人满世界购买口罩和防疫物资。这背后反映的其实就是阿里的组织能力。不同的个体,统一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认知“阿里人”。这是一个共同体。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形成,靠得都是信念、情感、理想。
决定组织能力的第二个要素,是创始人的的人际容纳度。
人际容纳度,是一个人能够容纳深度关系的能力。梁宁说,你能容纳什么样的人,你能和多少人建立深度关系,就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弹性和体量。
而想要进入深度关系,往往要经历四个时期。如果能够顺利通过四个时期,关系还没有崩溃,才能建立深度关系。
我们来看下这个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理想期。理想期很好理解,人和人在开始接触的一段时间,满眼都是对方的优点。这和我们谈恋爱其实是类似的,在恋爱初期阶段,我们处于蜜月期,根本看不到对方的缺点。
所以,这个时期对于彼此而言,是一段甜蜜时光。但是,遗憾的是,理想期不会持续太久。当我们和他人接触很近后,很快就会发现,对方远远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接下来,就进入了冲突期。在冲突期,我们会用放大镜去发现对方的缺点。然后,大部分人会开始没完没了的指责,内心充满被辜负的愤怒感。有些人则背负上了沉重的内疚感。
这个阶段,很多关系就会走向崩溃。受不了指责,承受不住内疚,都可能导致随时崩溃,从而引发分离、决裂。即使没到这一步,很多人也会开始选择远离、逃避。
在冲突中,不做评判者,而是把问题看做彼此的差距,然后一起解决问题,一起成长,就会顺利进入第三个阶段:整合期。到了整合期,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记忆,有了强烈的情感,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完成整合期,继续升级,走到第四个阶段:协同创作。共同体中的你我,愿意共同承担未知的风险,愿意一起前行。
机会砸下来,这个组织有能力接住。机会不只是机会,机会伴随着风险、不确定性,甚至是彼此信念的冲突。
只有能够完成整合的组织,才能接住美好而又危机四伏的机会。
04
选择高度契合的模式
发现机会,找到破局点,也有共同体了,事情可以启动了,但是还没有结束,对于企业来说,一定要选择一个高度契合的发展模式。
什么是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换成“系统”这个词去理解。在一个系统里,要有目标,要有要素,要素之间还要建立连接。
先设定好目标,接下来的重头戏是确定到底要有哪些要素,这些要素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决定了最终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可以说,发展模式,就是资源要素之间的配合方式。
梁宁谈了同样是做咖啡的星巴克和瑞幸,它们的模式差别很大。
对目前阶段的星巴克来说,首要目标是要做高端品牌,赚得是品牌的溢价。在这个目标的指导下,星巴克非常注重体验,始终坚持第三空间,大家到了星巴克,可以办公,可以休息,想呆多久由自己决定。
我每次到有星巴克的商场,离很远就能闻到咖啡香味。其实这是有意营造的氛围,代价是放弃了所有熟食生意,避免串味儿。进到店内,我们还能看到非常专业的服务员,工作服分了等级。这些都是星巴克刻意打造出来的专业度。
咱们再看瑞幸。它和星巴克是完全不同的模式。一个瑞幸咖啡馆的面积也就10多平米,里面没有座位。大家买了咖啡要打包带走,而不能像在星巴克一样优哉游哉品尝。瑞幸的一杯咖啡才10元钱,而星巴克均价在33元。
为什么同样是做咖啡,模式差别这么大?这是目标差异带来的结果。瑞幸的目标是速度,花钱带来流量,再用增长的流量撬动资本,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模式形成良性循环。
假如瑞幸也用星巴克的模式去发展,大概率会死得很惨,一个新品牌很难拼得过老品牌。
如果模式和目标不匹配,极有可能发生灾难性后果。比如雕刻时光,曾经被称为民族第一咖啡品牌。起步的基因是慢生活、文艺情怀。结果发展中忘记了当初的目标,开始追求速度,迅速扩张。
速度很容易带来混乱。雕刻时光的文艺情怀逐渐消失了,竞争优势也就没了。从创建到今天的衰落,让人不禁唏嘘。
另外,梁宁在课程中主要介绍了五种发展模式:以用户增长为核心的模式、连接器模式、整合模式、流量模式、产业中台模式。
以用户增长为核心的模式,比如keep,发展依靠的是用户的爆炸性以及持续增长。
连接器模式,是做一个连接的中介。比如,携程,连接了航空公司和用户,印度酒店OYO,连接了小酒店和用户,再比如早期的拼多多。
在连接器模式中,企业实际上是轻度参与,对用户来说,我只需要通过你做成一件事。用户不会花时间停留下来。这意味着,这个平台其实很容易被其他同品类的平台取代。
连接器模式可以转化为流量模式,前提是用户开始沉淀到平台。平台有能力形成一个流量池。一旦形成流量池,就可以为其他需求的个体提供曝光机会,提供被点击的机会。
在这两种模式中,企业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中介性质,只不过介入深度有很大区别。驻扎在各个平台的流量,仍然是一个个的独立品牌。
到了整合模式,个体品牌不再存在了。因为做了资源的整合后,新的品牌诞生了。比如同样是做酒店生意的亚朵,房东提供房源,亚朵会去改造房屋,去控制用户体验。最终的酒店,形成的品牌是亚朵,而不是单个的房东。
整合模式和用户形成了重度关系。亚朵有自己的会员,能形成品牌溢价,和房东的谈判能力也会越来越强,而OYO则只能做最普通的对接。
再来看产业中台模式,要完成更大型的资源整合和链接,需要企业有更加长远的战略眼光。
梁宁说美团正在成为餐饮业的中台。各个平台会借助美团的配送服务、大数据分析等资源。对各个餐馆来说,借助美团的流量、送外卖服务、大数据分析,才有可能完成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个人也要找到自己的模式。要做连接器,还是做中台?自己要和周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05
跨越周期,持续增长
梁宁在课程中,多次探讨了企业如何实现持续增长,甚至是跨越周期。对企业来说,其实想要持续增长,近乎于一个神话故事,尤其是跨越的时间周期变长后。
那怎么持续增长呢?
第一个方法:设计增强回路。增强回路是系统思维中的一个概念。系统中有两种反馈回路,其中一种是增强回路。
增强回路会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比如,如果你写得文章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就会去写更多的文章。当你写的文章越多,你的写作技艺也会不断提高,就更可能写出读者喜爱的文章。这就是一个增强回路。写文章-读者喜爱,这两者之间彼此增强。
对一个公司来说,如果存在一个增强回路,公司就很容易实现持续增长。
举个例子,我经常在万达的一个店铺购买各种小商品,口红、香水、水杯等等。口红一只35元,相当便宜,更重要的是还很好用。所以,我很快就注册成为了会员,购买的频率几乎是一周一次。
对店铺来说,像我一样的会员越来越多,购买的频次越来越高,那它向供货商压价的能力也就更强了,然后,商品就可以更便宜。结果就是,更多的人愿意来这里购买。这就是一个增强回路的形成。
对主营业务单一的小企业来说,能够设计一个增强回路,就可以持续增长。但是对大企业来说,往往涉及多个业务模块。要想实现持续增长,还要尽可能让不同的业务也能互相“增强”。
大家应该听说过亚马逊的“飞轮效应”。飞轮效应说的是不同业务之间,会形成相互推动的关系。
这就像一个飞轮,咬合的齿轮在旋转中会互相推动。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不同的业务,能够彼此“增强”对方。
我们来看下亚马逊的其中三个业务模块,如何形成了飞轮效应。
亚马逊有一个99美金的会员业务。花99美元成为会员后,就可以享受所有商品包邮。再来看第二个业务Marketplace平台,第三方平台可以入住亚马逊出售商品。这个模式和我们淘宝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淘宝全是地方平台。
第三个业务,亚马逊的FBA服务,第三方平台可以把商品寄存给亚马逊进行统一管理和发货。也就是说,个人没必要租库房,聘请发货人员。这些事务完全可以转包给亚马逊来完成。
我有个在美国的朋友,就是把自己的商品存在亚马逊,他只需要完成和客户线上的沟通,省掉了很繁琐的存储管理成本。
咱们看看这三个业务之间怎么互相推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产品越丰富,会员就会越多。
会员越多,购买产品的人也就越多,那就能吸引更多的地方平台入驻亚马逊。而FBA服务能专业化的服务于中小卖家。所以,中小卖家会更愿意入驻亚马逊。
而且,对中小卖家来说,亚马逊专业仓储的成本会远远低于自己去租房子,雇佣人员。这么一来,价格还可以再次降低。价格更划算了,自然会员也就更多了。
你看,这三个业务之间是不是像咬合的齿轮一样,始终能互相推动。一个业务变强,另一个业务也会随之变强。
一个企业能设计出自己的旋转飞轮,会更容易实现持续增长。
到这里还没结束,对企业来说,关乎生死的还有一个大问题:如何跨越周期。
梁宁说,大成靠周期,大毁其实也是周期。
毁于周期的例子,大家应该知道不少,比如诺基亚,柯达、惠普等等。
怎么跨越产业周期?或者说,当市场上风口变化的时候,怎么才能确保自己跟上这个风口,而不是被甩在沙滩上。
要去预测什么时候会有什么风口,这显然是比较玄学的事儿。真正要依靠的,实际上是系统的设置。
华为跨越了四次产业周期。我们来看看华为的做法。华为内部有蓝军部和红军部。
蓝军部代表竞争对手和创新模式,会模拟对手的商业策略。整个蓝军部专门做的事情,就是研究如何“杀掉”红军部。
什么意思?一个企业内部,诞生了一个部门,不停的去找自己的漏洞。比如说,一个产品出来了,蓝军就要负责唱反调,找漏洞。
这件事不需要竞争对手来做了,在企业的内部完成了。一个产品,或者一个企业方案,必须扛得住蓝军不遗余力的攻击,才能活下来,这也就避免了被外部真正的竞争对手消灭。
这种内部机制,可以帮助一个企业意识到现存产品的问题。如果当年柯达也有自己的蓝军,可能就不会雪藏第一台数码相机了。
华为是有专门的机构,而字节跳动则是发动了全公司的力量。字节跳动内部有一个论坛,所有员工都可以匿名吐槽公司的产品。公司内部还有一个“产品吐槽大会”,在大会上,员工会吐槽自家产品,赞美竞争对手的产品。
亚马逊在这方面的做法也很值得借鉴。贝佐斯认为,世界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测,真正的竞争对手往往在视线之外。所以,贝佐斯非常鼓励试错,鼓励创新。
比如Maketplace平台,就是试错试出来的。最初叫做亚马逊拍卖,卖二手商品,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又改成Zshop,还是不成功,最后才改成了Maketplace。
跨越周期,靠得也是扎扎实实的方法。有了方法,就有了希望。
对个人同样如此。我们也有要跨越的周期,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增强回路,生成自己的飞轮效应,也可以建立自己的蓝军。然后,完成演化。
06
尾声
增长,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永远是一个热门话题。这是所有个体以及企业,都渴求达成的目标。
梁宁的《增长思维30讲》课程,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寻找方法,永远比依赖运气更重要。
任何一个人如果愿意深入进去探寻门道,就不会再认为成败皆是固定的运数。
面对人生,我们可以更主动。
你可以选择做跨越周期的猛人,也可以选择做一个速生速死的路人。
这就是人生的魅力。自始至终,我们都有权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