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远川研究所
1931年,武汉遭了一场大灾。
华中地区从1930年冬季开始便大雪不止,第二年春季,融雪汇集了没断过的梅雨,让江淮地区的河流水位逐渐上涨。到了7月份,长江流域更是连降20多天的暴雨,整个湖北境内江河湖泊几乎全部溃堤,而当时被称作“东方芝加哥”的武汉,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城市。
水灾在8月中旬迎来了最高峰,偌大条长江的水位比汉口的堤防还要高出了1.6米,武汉三镇淹没于水中长达3个月之久,整个汉口更是成了一片汪洋,最高处淹到了三楼。仅溺水而亡者就有2500人之多,每天因中暑、饥饿、瘟疫等次生灾害而死亡的人超过四位数。

被淹的武汉中山公园,1931年
武汉受灾后,《申报》《大公报》等媒体连篇累牍刊登赈灾启事,号召全国支援灾区。不过在政府缺乏财政能力和基层组织的年代,救灾举步维艰,南京政府只能通过贷款的方式从美国买了45万吨小麦,并强制全国公职人员捐款三个月,才为救灾筹集到了部分物资。
在熙熙攘攘的救灾前线,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划着小船收治痢疾、霍乱患者的武汉协和医院。
三年前刚刚由仁济和普爱合并而成的武汉协和医院,在教会资金的支持下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医院之一。在水灾前期,协和大量收治灾民,但后来水位渐涨,协和的主院区被淹没,医护人员只能困守孤岛。停电加上缺水,让这所华中地区最大的医疗机构也难以为继。
幸运的是,身处绝境的协和遇到了上海国际洪灾救援会,在后者的帮助下,协和在上海租下了一条3300吨的运煤船,每月租金和维护费用高达25000美金。协和把这艘船改造成民国版“方舱医院”,专门收治水灾下的瘟疫病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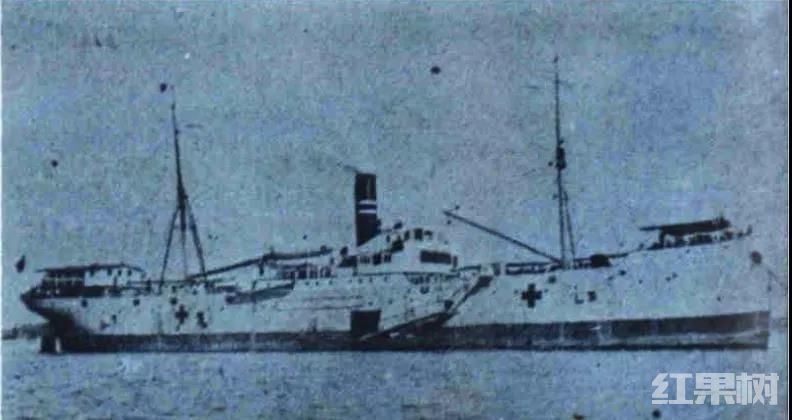
协和租用的“罕拿摩勒号”医疗船,1931年
医疗船上除了有手术室和药房常规设备之外,床铺、被褥、床头柜等小件东西也一应俱全,为了方便救治,协和院方甚至将一间细菌实验室也搬上了大船。从投入运行到结束,一共有628名病人在医院船上得到救治,其中大多数都是“接近于赤贫的中国病人”。
89年后,新型冠状病毒侵袭江城,历经变迁、起伏和沧桑的武汉协和医院再次成了救灾的主力军之一。在两个多月的高强度压力下,武汉协和医院共收治了5200多人次的新冠肺炎患者,接诊发热患者超过2万多名,管理两家方舱医院,成为武汉市收治人次最多的医院[8]。
奋战在武汉前线的,不止有武汉协和,还有跟它齐名的武汉同济、北京协和、上海瑞金、长沙湘雅、成都华西、山东齐鲁等中国顶级医院。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些常年活跃在“中国医院排行榜”前列的顶级医院们战斗在了一起,它们是中国医学水平的最高代表。
回到1931年那场大水,武汉人民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逐渐撑过了那场劫难,而大水过后的汉口协和医院,也在原来的遗址上完成了重建。1931年的武汉洪水记忆,很快就被淹没在随之而来的民族救亡战争的硝烟中,但像协和这样的中国顶级医院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中国顶级医院的前世今生,就是一部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史。
01
说起中国这些顶级医院,有一个始终绕不开的名词:宗教。
早在1866年英国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在汉口建立仁济医院(武汉协和的前身)之前,他就在刚开埠的武汉设立礼拜堂来传教,但他碰到一个普遍问题:中国民众更渴望肉体的治愈,而非所谓的“灵魂的救赎”,于是教会办医院,就成了传教的唯一出路。
但杨格非还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1835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在宣扬新教时,清政府正实行禁教政策,严格限制传教士与民众接触。于是,裨治文在广州新豆栏开办了“眼科医局”,借此传教。这家医院便是今天广州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也是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
同样的还有上海瑞金医院。1903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姚宗李(Próspero París)为了扩大天主教影响,在教会支持下买下了上海法租界1.65万平米的土地来开办医院,取名广慈。到1925年,广慈医院的床位一度发展到500张,成为当时“远东第一大医院”。
教会医院刚开业的时候,大多数国人并不想“将身体交给洋鬼子宰割”。广州眼科医院设立的前一周都鲜有人来问诊,爱德华·胡美(Edward Hume)创立的雅礼医院(湘雅前身)在收治首例病人时,还有一群人挤在手术室外等待坐实洋人以治病为名残害国人的罪行。

长沙湘雅医院,1937年
但对于那个历史时期的人,生存比偏见更重要,再加上传教士们免费施诊送药行为的叠加因素下,胆子大的成为第一批享受“先进西方医学”的人,他们也成了教会医院的活广告。之后,吃瓜群众才开始慢慢接受医学传教士的诊治,而这其中有不少官员士绅等上层阶级。
而受惠的精英人士们会主动为基督教提供资助和保护,这奠定了许多地方传教事业基础。对此,美国一位作家感慨道[2],“欧洲的大炮尚不能拉开一个门闩时,手术刀却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有着“科学”+“慈善”双重属性的西医医院,则成了各界重点资助对象。
比如上海广慈医院每年都收到法租界公董局几十万银元的资助;北京协和刚建院不久,就请来了胡适、张柏苓等人出任顾问;1913年毕启(Joseph Beech)在建立华西医院时,筹集到来近400万美元的捐款,他用这笔钱聘来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不远千里入川教学。

毕启与特聘文科教授的合影,成都日报
1928年杨格非在扩建武汉协和时,看上了中正大道(现武汉解放大道)一块全是湖塘的洼地,并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准备进行还价。刘听说是为了建医院,直接让杨格非乘坐一条船,撑一桨后,船划到哪里,哪里就是医院的边界[3],全部免费。
有了教会和社会上的资金支持,并且这些传教士创始人本身在医学和社会界的影响也不低,这些数量并不多的医院们很快就吸引到一批来自哈佛、约翰霍普金斯、巴黎大学等高校医学院的顶尖人才,这让其诊疗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代表着国际最先进水平。
在国家积贫积弱、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匮乏的时代,这些医院本是西方传教士在“藉医传道”过程中播下的种子,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的现代医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逐渐吸引到了财力、科研、人才等资源的集中,一举成长为民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02
五四运动掀起了一场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大讨论,医学作为民生之一,自然成为最热门的议题。在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的争论中,鲁迅、陈独秀、严复、梁漱溟等进步人士纷纷高调为后者站台。但其中,有一位用生命来维护现代医学名声的人,他便是网红改革家梁启超。
1926年,梁启超出现了尿血症状,他怀疑自己罹患癌症,便去北京协和做了X光透视(当时最先进的检测设备),院方给出结论是肾癌,院长刘瑞恒亲自手术。切除肿瘤后梁的症状未见好转,其弟梁启勋在报纸上大肆指责协和,徐志摩等人抓住机会疯狂撰文批判西医。
虽然事后经检查发现,梁启超患的是一种血尿症而非肾病,属于院方的误诊,但病人救治细节属于隐私未公开,这件事被好事的人传成了:协和医生不分左右,切掉健康的肾导致了梁的去世。这个桥段被姜文拍进了《邪不压正》里,用来讽刺当时盲目抵制西方的保守派。

和彭于晏握手的是协和院长刘瑞恒,《邪不压正》
而当事人梁启超却几次三番站出来维护协和医院,称“我身上的情形只是一个意外,北京协和医院正在对中国的进步做贡献,我们不能因为科学发展尚不完善就指责科学本身。”梁启超作为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在当时文化碰撞背景下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西医的名声。
北伐战争后,“割错腰子”的协和院长刘瑞恒弃医从政,成了蒋介石的第一任卫生部长,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反对给传统医生颁发行医执照,态度强硬。这种做法太过极端,遭到了传统医学界的强烈反对,他们一直向南京政府请愿,终于在1935年得到了认可。
但知识文化界对传统医学的批判一直没停过,直到最后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的观点被编进了《语录》,这场新旧文化之争才逐渐平息。虽然彼时社会对中西医的态度莫衷一是,但对于这些教会医院的诊疗水平,社会精英和上层人士生病后,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蒋经国在发现好友的胃病久治不愈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时在湘雅的张孝骞;而作为“远东第一大医院”的广慈医院,是上海滩大佬和南京政要最常去的地方;不过对于在广慈暗杀过陶成章的蒋介石来说,由孔祥熙和宋子文亲手建立的上海中山医院,似乎才是更好的去处。
而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手笔布下的北京协和医院,则更是社会名流们最爱的疗养院,孙中山选择了其作为“人生的最后一站”,张学良也在这里吃过住院餐,宋氏三姐妹都有病例保存在协和的病案室。

北京协和医院,1934年
和武汉协和医院在水灾中拯救穷苦患者一样,北京协和除了接待权贵们,很多医疗资源还是留给了平民百姓。北京协和当时在挂号处设立了一个分诊台,分ABCD四档,CD档经常减免甚至完全不收患者费用,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社会服务部,专门为贫困者提供经济支持[4]。
但不论是协和还是湘雅,最大的问题是“医生产能不够”。这些教会医院的医生培养模式大都是“精英教育”,要造就“世界医学领袖”而非“二等医学公民”,教学标准直接对标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这种高进严出的模式下,每年医学院毕业人数不超过两位数。
不过彼时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几百个医学领袖,华夏大地缺的是几万名几十万名现代医生。主流舆论希望这些顶级医学学府能够扩大学生人数,这遭到不少教会医院的反对,他们认为质量和数量二者不可兼得。然而这场争论还没来得及广泛讨论,时间就拉到了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教会医院因为理论上属于西方国家的财产,医院尚能继续运行。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和欧美国家全面撕破脸,国内大部分教会医院都没能幸免。广慈医院一半的院区被征去当做日军的野战医院,中山和仁济的院长也都换成了日本人。
而内地城市的医院就更惨了。战时的长沙湘雅医院全部被毁,院长张孝骞领着众人西迁重庆;广东新公医院(现广东中山一附院)在1939年就被被迫迁往云南澂江;北京协和院长、总务长悉数被日方监禁,大批医护不得不跟随南下队伍,穿过层层封锁,逃往了西南。
协和的内科专家李宗恩来到贵阳办立新的医学院,生理学家林可胜辗转几座城市后跟随远征军亲赴缅甸担任军医总监。在这一批远赴西南的“老协和”中有一位叫钟世藩的人,当过南京中央医院的儿科医师,后来成了中央医院贵阳分院院长,有一个儿子叫钟南山。

贵阳中央医院(如今的贵阳金阳医院)历任院长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些中国顶级的医生们离开教会医院分散到偏远的土地上。虽然院区在战火中被毁,但对于一家医院来讲最核心的要素还是医生。1945年日本投降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名医们纷纷回到原处,这些顶级医院们很快就在被摧毁的原址上重现了辉煌。
但面对改天换地的历史潮流,这些包含“帝国主义”元素的教会医院需要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03
70年前,武汉向上海借来一样特殊的东西:同济医学院。
1950年,建国初的六大区之一的中南六省(湘鄂粤桂豫赣)人口超过一亿四千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行政大区,仅有的协和、湘雅等医院满足不了亿万民众的卫生需求。于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长孙仪之提了一个建议:希望医药卫生发达的上海能向中部地区提供援助。
彼时中南区的主席是林彪,这一意见很快得到中央的支持。考虑再三后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最终同意将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中美医院打包送给了武汉。医院后来改名武汉同济医院,和武汉协和一起成为了华中最重要的两家医疗机构,长期位列“中国医院排行榜”前20名。

搬迁到武汉的同济医学院,1951年
建国后的中国医院管理完全照抄前苏联:教学要和诊疗分开,并全部由高校来组织,医院花的钱全部国家出,所有的医院归军管会统一安排[5]。而这些原来隶属于宗教和基金会的医院,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公立医院。
军管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医疗失衡的问题”,直接搬医院毕竟太费周章,挖人才是更好地选择。朝鲜战争期间,北京应要求组建301医院,挖走了三分之一北京协和的医生,甚至连电话员、病案室成员都没有放过[4]。
不过新中国的成立点燃了海外留学华人的报国热情,不少像钱学森一样的高知分子投身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其中不乏一大批医学领域高材生,而原来的教会医院本身就是前沿医学的象征,它们很好的承接了这批人才,这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这些医院的医疗水平。
人才资源问题解决了,但时间问题上仍然严峻,20年前关于“精英教育”的争论再一次被提起,彼时国内就算算上赤脚医生,卫生从业人员加起来也不超过20万,而总人口超过五亿,全国范围内的医疗体系几乎不存在,在那个年代,花八年时间培养一名医生实在过于漫长。
但这一次问题仍然没来得及讨论,时间便来到了1966年,“富含资产阶级色彩”的教会医院遭受严重冲击:广慈医院被改名成了东方红医院,华西医院的医学课程大部分换成了军训,同济医院的病例教研室完全被毁,连主席最喜欢的湘雅医院,其医学院也遭到停办。
不过,遭受浩劫最大的还是北京协和。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的家成了“革命造反派”的据点,流行病学先驱何观清因反对苏联专家的观点被拉上台批斗;协和副院长胡正祥在被抄家毒打后自杀身亡[6],而就连红色背景颇深的黄家驷也被发配去了江西五七干校喂猪。
文革期间大批医生被下放,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其它地区的医学水平发展,不过在各个医学院停办的情况下,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人才补充停滞了整整十年。但好在北京协和医院历史底蕴足够雄厚,其地位才不至于被撼动,能够继续新中国输送一代又一代的顶级医学人才。
而1978年邓小平宣布恢复高考以及研究生教育项目后,医院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04
北京反帝医院在改回“协和”之前,还叫过一段时间的“首都医院”,这和一个人有关,他是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2月,在尼克松确认即将访华后,北京反帝医院作为最大的接待外宾健康需求的医疗机构,周恩来便联系军管会一起商讨改掉这“不友好”的院名,更名为首都医院。因科学交流之需,改名同时医院也召回了大部分正接受“改造”的专家。
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握手预示着这场交流顺利结束,而经此事的“首都医院”在周恩来等人的干预下得以从文革中回归常态。伴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首都医院在1980年重新改名为北京协和。中国的公立医院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中美建交为中国的顶级医院们重新和国际接轨提供了一道契机,独自龃龉前行了三十年的国内医学,得以再次和世界前沿同步前进。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这些百年医院成了中国各类医院排行榜上雷打不动的常客,他们是中国最顶尖医疗资源的代名词。
1992年,在中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医疗机构也被卷入了这场改革浪潮中,这些顶级医院在被叫了近半个世纪的“公立医院”后,迎来了五十年来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词汇:医疗市场化。
但和70年前有着基金会资助的私立医院不一样,医疗作为最大民生行业,在没有任何机构的约束下将医院完全企业化,会无限制滋长其追利的本能。这个制度很快就随着非典这只黑天鹅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而被叫停。
但崇尚市场的改革家认为这是税收、编制、科研等体制资源未完全放开的结果。于是医改之路的探索在继续,关于医院公立化和市场化的讨论仍不绝于耳:一方面是站在宏观角度,想要用万能的市场所有问题,另一方面是从道德方面认为就医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需求,公平最重要。
作为中国医疗机构的巅峰代表,同济、中山、湘雅等成为医改家最乐于研究的对象,“该不该卖掉协和”成为学者们最热衷讨论的问题。卫健委和人社部等利益相关机构则围绕这些问题上线一项项政策文件。
在这一收一松的拉锯战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原本就坐拥顶级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抓住全民医保释放出的巨量就医需求,依托体制优势从医疗水平(科研)、规模(床位)和支付端(异地医保)三点出发进行改革,一举成长为超级医院。
华西和郑大一附院两家医院将这一模式推向了高潮,瑞金、华山、齐鲁等同样在这个模式中吃到不少红利。因此尽管限制公立医院规模的文件汗牛充栋,但国内的大医院在补供方和补需方之争中,趟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2012年,就在外界对公立医院无限扩张模式产生质疑时,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来郑大一附院考察,逛了一圈,只说了一句[7]:“病人有需求,郑大一附院全力满足,这并没有什么错。”
关于中国医疗体系的改革,各方都有各方的观点和要解决的问题:大医院发展带来的其他周边医疗资源的空心化,公益性导致的医生高强度工作和人性关怀的缺失,以及八年制的医生培养速度和日益加重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
但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没尝试回答过:就是如何用有限医疗资源,去买无限医疗需求?
之所以没有人回答,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

长时间工作的医生因为低血糖正在喝葡萄糖生理盐水,2016年
然而,在这些野蛮的经历过后,协和仍然是当年的协和:代表着国内最顶级的治疗水平,每年培养一批又一批的高质量年轻医生,从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阶层的患者……
而瑞金、同济、齐鲁……这些其它城市的“协和”,他们同样脱胎于教会,参与过新旧主义思潮的大辩论,走过战争岁月的坎坷,经历过文化大运动的洗礼,并投身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进程,在一百年的近现代史中,最终成长印着中国烙印的顶级现代医院,承担着无数老百姓的医疗需求。
公立医院们是守护中国老百姓健康的第一道门,同时也是阻挡死神的最后一道墙。
05
2020年1月26日,武汉疫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绪。北京协和医院派出一支由21名医务人员驰援武汉,并在之后陆续增兵,派出更多的医疗队。此后,华西、瑞金、齐鲁、湘雅纷纷迎头赶上,有四家医院于2月7日同一天到达武汉,被媒体称为“四大天团会师武汉”。
这时,知乎上关于公立和民营医院的话题又热了起来,“如何看待驰援湖北的几乎都是公立医院”这一话题引来了150万用户驻足浏览,其中一个“相比于私立医院,公立医院不避嫌,主动接收肺炎疑似患者”的回答,足足吸引了近1.8万人点赞。
前卫生部部长陈竺在解释公立医院时曾这样说到:“公立医院是体现公益性,解决基本医疗,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的主体。”
回到自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那场争论:中国的顶级医院到底该选择“协和式教育”还是更多考虑患者的需求?这个问题在21世纪似乎有了答案: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们,以其勤劳的汗水,既在学术上做到了与全球医疗水平齐头并进,又全方位地保障了13亿人的就诊需求。

一名武汉警察向离开的协和医疗队敬礼,2020年
2020年4月15日,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15日完成了使命,奉命返回北京。这只医疗队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整建制的接管重症ICU病房,扛过了压力巨大的整整80天,他们是最后一支撤离武汉的国家医疗支援队伍。中国的顶级医院们,完成了一场口罩下的检阅。
无论是在前所未有的老龄化进程中,还是在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里,中国顶级医院和它们背后的公立医疗体系,始终是民众最坚实的后盾。













































































